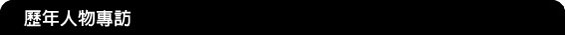「我想The Libertines是音樂生命裡,一個很棒的橋段。」
我正坐在前The Libertines,現在為Dirty Pretty Things(以下簡稱DPT)鼓手的Gary身旁,他抽著萬寶路淡菸,是第一個來到訪問現場的團員。也因為他的早到,身為採訪者的我可以很驕傲的說,Hitoradio的DPT訪問,比起其他媒體,絕對超exclusive。(因為我當場就把他抓來聊了。)
來到野台開唱擔任壓軸團前,DPT發行專輯,並展開密集的巡迴。前一站是日本,野台完畢後他們將回到倫敦,然後再次密集巡迴美國。
「一路巡迴,我簡直像被油炸過幾翻了。」,他面露些許倦容,喝著一壺綠茶,當我問及關於轟動英倫的The Libertines以及話題主唱Pete Doherty相關問題時,他顯得相當健談,我還深怕闖到地雷區。
「在The Libertines時期,學習到了很多與音樂與人相關的事情,那些東西是我從來沒有想過,成為一些什麼,以及被他人如何看待,而我們一夥人一起嘗試將音樂作得更好的過程。不幸的是,後來有很多事情完全超出我們的掌控,媒體有許多胡言,很多事情在後來看來是一團糟。我必須說,在The Libertines的告別巴黎演唱會中,我們跟Pete有著很好的互動,我們在日本和波士頓以及其他地方,我們有很好的共同的回憶。不過英格蘭媒體真的是相當的……」
病態?
「絕對如此。報導總是,不知道哪裡來的或者無來由,然後呈現著懶惰與無趣──讓Pete顯得像個落水狗,而這整件事情讓人氣餒;沒有媒體認真的看待關於Pete的其他事情,寫歌、寫詩,繪畫,但媒體只針對一些部分去做報導,而那些報導相當無趣:Pete又吸毒了,Pete又被逮捕了。我知道他吸毒,但這算哪門子「新聞」。有一次我朋友打電話來,劈頭就問:你聽說了Pete的事情嗎?我說沒有。『什麼?你沒有!』,我說,讓我猜猜,他被捕了?『你怎麼知道!』,拜託,要不然還會是什麼!這些懶惰的英格蘭媒體,根本就不算在做報導嘛。」
所以你們仍與他有聯繫?
「沒有。我上次看到他是去年九月,我在巴黎DJ,在場的還有Alan McGee,我跟他聊了大概五分鐘,他有提到他正試著戒毒。我真心希望如此。」
回到DPT,我們聊到團的巡迴,正是從巴黎揭幕──那同時是The Libertines的告別演出,對於陣中尚有兩名The Libertines的DPT而言,這是否意味著什麼呢?
「這其實應該算是我的主意。我們從那裡結束,重新開始時,也想在那裡──這說得上是讓人們看見我們回來了的理想方式。」Gary完全認同我所言:樂迷看見一個新團的誕生,但事實上是重逢的老友。
「如果你是The Libertines的樂迷,你應也會喜歡這張專輯」當我提到我對The Libertines的喜愛,同時也深受DPT的專輯撼動,Gary肯定的表示。「製作和編排上或有不同,但本質上的氣氛差距不大。」但更多了些旋律性吧?「沒錯,更具旋律性。許多歌曲都有著很吸引人的曲調。」
說到旋律性,我正想著樂團主腦Carl什麼時候才會到來;此時主唱Anthony以興奮而熱切的語調向場內所有人打招呼。並在我身旁,把滿滿兩湯匙的糖加入綠茶內。「噢∼真是好喝哪!」
「Anthony,熱血角色。Gary,慵懶角色。」Gary笑著說。 |
我開始問一些關於DPT的「問題」,在此前比較像是閒聊(事實上後來也像是吧)。「所以不會再有關於茶的問題了嗎?」Anthony開我玩笑。
NME曾在現場演唱評論中撰文玩笑到,DPT今夏有一千多場的演唱會,所以能看到他們如此有活力真是太棒了。事實上,怎可能有一千多場,不過成軍後,確實相當密集而世界性的巡迴著,在英國、歐陸與世界各地大小音樂節無役不與。
Anthony:「挺累人,以前從來沒那麼密集的演出過。不過我覺得很幸運的,專輯發行後,很多人去買,然後表演中我們很快的能夠跟大家取得共鳴。」Gary則說到最大的挑戰是不管到哪哩,在什麼天氣之下,團員們都必須相依為命,並嘗試在舞台上做出最好表現。
「最糟糕的演出經驗?」兩人指出發生在紐卡索(Newcastle)某個我沒聽過的音樂節。「那種雷霆暴雨的天氣下,舞台看來像是要垮了,甚至沒有準備食物給樂團,整個陷入瘋狂狀態,場子好像沒人管似的。在蘇格蘭有人在表演時潑尿,『想喝尿嗎?來點尿吧』他們大概覺得那很好玩吧。」;「最糟的大概就紐卡索那回了」Gary重申,「我被天雨而來的亂七八糟遮蔽物搞得幾乎沒法子表演。」。
那麼最棒的呢?兩人思考一陣,「嗯……我們首次英國巡迴時,有次在里茲(Leeds),實在有夠小的場地,但演出氣氛超火燙,舞台效果也完全呈現,全場擠爆,那是我最喜歡的演出之一。」Anthony先回答著。「我試著不去定義何者最佳或最糟,多數時候與群眾的互動上,不管群眾以什麼方式呈現他們的熱情,而甚至必須去忍受,我想互動過程還是最重要的。」Gary如此表示,Anthony表示認同,有時候人們對於表演的感受相差甚大。「能看到樂迷們知道這個團與歌曲,跟著唱和,而我們試著盡情與他們互動,我們很幸運的,都算是在此般狀況內。」 |
巡迴途中有沒有同行的樂團,讓你們印象深刻?「多數樂團都是我們的朋友,跟他們表演總是榮幸而愉快的。」那麼當今英格蘭有沒有什麼吸引你們注意的新團,比方說最來大熱的……The Kooks?
「我喜歡The Kooks,他們有些不好的名聲但其實人還OK…」當Gary這樣說著時,Anthony笑著對我說他其實根本還沒聽過任何The Kooks的歌曲,「他們的音樂或許有點……制式吧,但就算是這樣,在舞台上的器樂表現以及專輯呈現都不錯。」Anthony提到來自牛津的The Young Knives,覺得其具有黑暗生猛的力道,「有些人或會說他們是模仿團,但你知道的,重點不是這個。」
現場演出時,最讓DPT本身感到興奮的歌曲是哪一首呢?”You Fucking Love It”?
「眼前我會說是”The Enemy”跟”Gin and Milk”。”You Fucking Love It”之所以振奮是因為全場會一起唱You Fucking Love It,那情況比較像是注射古柯鹼」「嗯,注射咖啡因。」「”The Enemy”跟”Gin and Milk”比較多其他因子。」Anthony跟Gary相繼回答後,吉他手Carl與貝斯手Didz終於步進房間。
很可惜的是,時間緣故,Carl真的回答到的問題並不多。身為The Cooper Temple Clause忠實樂迷的我,對原本來自該團的Didz亦有很多好奇。
Carl表示,DPT是一個友誼聚合與器樂凝集的動能呈現,「對我們來說,這一開始就是很簡單而直接的計畫,就是我們想要有,好,比方說三把吉他,然後根據歌曲的根本去發展出樂團的類型。不管那是龐克也好或是搖滾,我們有著動能去詮釋,然後其實很直接了當的彈奏。基本上從歌曲去發展。」Didz說,「對我而言,這張專輯絕對是前所未有之具有能量的。雖然,很簡單的就是彈奏搖滾樂的基本樂器。」
Anthony :「我們絕對不是做場團,也不是嘻皮團,不擺撲克臉,也不跳探戈。」
Gary:「我想我們都朝向同一個目標而前進,因而有現在的DPT。」
對於外界也將DPT視為Carl的「新計劃」,身為這個樂團的主腦,Carl操著厚重東倫敦口音淡淡地說,「應該說,我很專注於這件事情上面。的確是我把這計劃型塑出來的。」
Didz說到,好像有個詞彙曾被套在DPT上,Gangster Rock。不過在場包括我再內所有人都不了解那到底是什麼。
音樂偶像呢?Carl提到六零年代末期的鮑伯狄倫,「一些橋段與風格……雖未必稱得上是偶像。不過確實有著影響。」他回答問題前總思考許久。Didz則提到Stone Roses的Mani。
最後的時間裡,我們聊了足球,以及他們即將前往美國的感受。
「現在到美國,是很好的時機點,我們在其之外的地方已經足跡踏遍。這次我們會找的一個新的美國。我們知道那裡有什麼,我們有什麼,而這讓人期待。」Anthony果然是最熱血的角色。
跟我一樣是足球迷,同時也是DPT的樂迷們,以下是團員們的支持球隊:Carl──兵工廠(跟我一樣,害我訪問時差點失態。)、Didz──卻爾西、Gary──維根(Wigan),Anthony則是巴塞隆納隊的球迷。
雖然四個團員支持的球隊時在稱不上有交集甚至有點衝突,但他們對於英格蘭隊在今年世界盃的表現卻抱持完全一樣的看法──還可以好上更多才是。
「誰的錯?」
Didz:「C.Ronaldo的」;Carl:「裁判的。」;Gary跟Anthony:「十二碼罰球練得不夠多,總是這樣……」
| |
|
|
| |
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