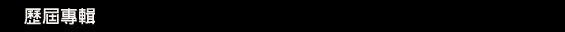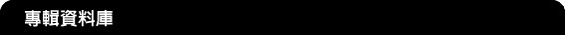|
|
|||||||||||||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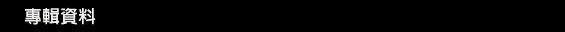
| 離開銀色荒原,是一場「意識逃離」的紀錄。 一切始於一對戀人跨越百年的重逢——他曾將自己凍結於時間之外,為等待戀人從機械的身份蛻變為與他同質的“人”。他們約定在醒來之後,於永恆的未來中重逢。然而,當相遇終於落入停格的永恆中,愛卻因失去流動而逐漸衰敗。在剝奪了消散與變化的“銀色荒原”裡,一切都淪為乏膩的重複。 這是人類“意識逃離”的起點。 他們開始渴望潰敗,渴望短暫,渴望那些會消逝的觸碰。他們穿越銀色荒原,去尋回被遺落的“自然”。 這注定是一段迷人的旅程,無人知曉他們是否真正抵達,卻喚醒著我們對生命流動的再次感知。 或許,離開銀色荒原,本就沒有目的地。在他們彼此陪伴的追尋中,時間已重新開始流動。意識回到這段被完整書寫下來的記錄。 ———————— 冬眠前最後一次去水族館,他對著金魚閉目許願。 機器的戀人在身旁沈默不語,待他結束才開口詢問:“你想要怎樣的未來?” “我祈求永遠,”他與那深藏鏡頭的雙眼對視,“祈求你我同是人類,永恆相守。” 傳說中的金魚為漁夫實現願望後,又因人類的貪婪而收回了饋贈。面前的金魚兀自游動,冒昧的人類莫名陷入不安;三個願望,算是貪心嗎?會轉而變成詛咒嗎? 他們徘徊直至閉館,在磁浮列車的站台告別,準備開啓一次遙遙無期的分離。他向戀人遞去一封信:“用極難分解的塑料製成的。我不敢賭任何的電子存儲介質……但寫在紙上的字總可以直接讀取。” 信上寫明瞭名字和愛戀,還有一句約定:“未來見。” 短生的人類陷入沈睡,不計年的機器投身變遷。時間開始變作巨大的、無休止的加速器,直到把世界推向某一個進化分支的頂點才能暫停。機器也終於成為符合此刻定義的“人類”;他們終於可以相聚,可以獲得永生永恆的愛了。 他醒來得見的就是這樣一片安寧純淨,沒有錯拍或即興,無需複雜的合成代謝:銀色無休地鋪展著,永遠成為萬物的材質,一切凸起的部分——樓房、植物,乃至人類——只像是這片銀色上小小的褶皺。 重逢在這樣的銀色裡很美……但隨之而來的是因恆定而生的疲倦。一切都很好,面容、體溫、心跳,穩固不變,如同常數。可是愛呵,愛需要的是那一點驟生的波動。曾是機器的戀人瞭解永遠比愛多;而一直是人類的他瞭解愛比永遠多。永遠和愛的疊加令他們都陌生到不知所措,他們長久對視,再也生不起波瀾。 找回愛的唯一線索是那封久遠的信件。舊時代的一切都已模糊,唯獨只在這封信件的文字裡,尚且留有關於鮮活、脆弱、激情的痕跡。他們讀信、回憶,想起曾被果汁弄髒的手指,終於喚起了牽手的慾望。 舊時代的人類第一次牽手是為了離開伊甸園。現在,他們要離開銀色荒原。 “我們會再次失去這種感覺嗎?”戀人的面容上殘存著屬於自己的第一道淚痕。 他從胸前的口袋裡掏出一顆生鏽的螺栓:“那就沿途把它都寫下來。如果找不到那樣的地方,起碼在返程時,我們還能記起。” 以荒原為紙,他們寫信。戀人接過“筆”時遲疑了一下:“這是……我過去的零件?” 他笑:“是,位於你的肋骨。” 那種動搖如影隨形;但兩人還是踏上旅程。到處都是靜息的死地,自銀白過渡到鐵灰。他們倒像兩粒特殊的塵埃,像餘燼在往火裡走。 火並不遠。驟然間,他們遇見了第一道生機:火山爆發,紅亮的熔漿噴湧,像劇烈跳動的心臟。接下來便是火山灰:蒼白的、冷卻的、熄滅的灰。明明一息之前還像心臟裡迸發的熱情,也沒有更驚天動地的奇觀在發生,就這麼平淡地步入成灰的結局了。 “和他一起我便看不見灰了,”在灰堆裡戀人寫下第二封信,“現在我只看到火。我想我們仍在火裡。” 前行,一同前行——世界似乎在為他們變好。一片春天中他們走了很遠。可在比很遠更遠的地方,兩個人仍只能在春天打轉。草木萌發但不生長,浮冰只融化到一半;杜鵑一路都開著,開到要確認那是不是假花。 倦意也沿著花海捲土重來。他們欲言又止,最後還是他先提出:“我們試試分開……分開走一段?” 分開的兩個人繼續於春天重逢了十七次。一開始在下一個花枝就能遇見;花朵漸漸密起來,要走過一大片才遇見;再後來是走過山、走過林……第十八次見面的時候,他們幾乎同時開口:“我很想你。” 春風突然變了,更暖熱、更潮濕,帶著水星兒;杜鵑也成片成片地凋落了。這時他們彷彿才意識到:那花真美啊。 第三封信就寫在花瓣上,一鬆手,就隨初夏的風飄得漫天都是,又在未知的各處輕輕委頓了:像一些渺小的絮語,拼了命地在太過短暫的話音裡告知愛。 生命開始變得有限了,他們各自這樣想著,應該說再多些,再多些。 但兩人終究還是把話在逐漸凝滯的空氣裡說盡了。世界似乎又從輕微的流動退回了永恆。 戀人突然說:“來吵架吧!” “我們大吵一架!” 當戀人還是機器人的時候,他們從來不曾爭吵過。機器人的底層規律是屈從——他突然想,那是愛嗎? 如果愛被設定為底層的代碼,你屈從的究竟是洶湧的情感,還是冰冷的指令? 吵!爭執!惡語相向! 在前所未有的歇斯底里中,一個風暴逐漸成形,席捲而來。狂風肆虐,他們狼狽地向對方嘶吼著,驀然看見一隻鳥歪歪斜斜地從風暴中飛過,像傷口,也像針腳;既流血,也愈合。 在飛鳥落下的羽毛上戀人提筆:“我剛剛才確認那絕非是他為我構建又寫入的……它真實地划過我的心了。它屬於我自己。” 啊,剛剛。那樣長的時間過去了,甚至已經接近永恆,可竟是剛剛確認真實相愛。 前面的景色很快又變成沙漠,一望無際,不辨方向。他取水回來,看見戀人被一群裹著樹皮的人圍住。 “奇卡奇卡,”那些人發出聲音,“奇卡奇卡,奇卡奇卡!” 雙方無法溝通,陷入了難解的困境。雖然對方友好地將他們一直送到沙漠邊緣,但語言的鴻溝還是無法跨越。戀人試圖在沙丘上寫字:“奇卡奇卡!”不一會兒,就被吹來的沙子掩蓋了。 他問:“你寫了什麼?” 其實戀人也不知道那是什麼:如果一個部落的全部語言只是“奇卡奇卡”,那具體它代表“你是誰”還是“我很餓”,好像都沒有區別。或許那也是“我愛你”。 是“附近有綠洲”,戀人答。 在作為機器人的全部時間裡,戀人都坦白得一覽無余;而人類會偽裝。戀人第一次嘗試這項技能,並用之於愛人,這才恍然意識到那些甜蜜過往多少沁著些許人類特有的虛偽。自己所愛的那個人類是如此擅長,甚至戲稱為“變色龍”都不為過,令曾經身為機器人的自己無法分辨。但現在……他們都是人類了。 接下來的旅途中兩個人開始像舊日的角色扮演遊戲一樣互相較勁。人設換了又換,深情戲碼雖然換湯不換藥,倒也高潮迭起。誰會先撐不下去?誰才是那個沒那麼愛的人? 直到他們真的目睹一對變色龍。沒有對外界的警戒,也沒有對彼此的示威,變色龍只是靜靜地挨在一起,呈現著近乎一致的本色。 這便是第六封信:一種如無意外還能綿延許久的動物,其本身就是一封耐讀的信。他們為這封信擁抱了一會兒。 現在他們已是彼此相愛的、勢均力敵的兩個人類。可他剛開始愛的時候……愛的是一個機器人。他曾像牧羊人一樣左右著這乖巧的機械羔羊。羔羊向他回報以盲從的忠誠,亦步亦趨,不曾稍有偏離。時過境遷,羔羊已不是羔羊。 或許應該讓羔羊自己選擇一次。 他策劃了一次不告而別。 藏在山坡背後,他窺視著戀人的一舉一動:閱讀了他留下的第七封信,清理了露營痕跡,環視四周,最終向原定的方向走去。沒有哭泣,沒有憤怒,似乎也沒有輕鬆。 他長出一口氣,在荒地上沈沈睡去。 只是命運總這麼荒謬。雨後的密林小徑昏暗又重複,轉過又一個相似的彎,他們又見面了。兩個人一前一後地走著,撥開藤蔓或灌木,踩碎斷枝的聲音在沈默裡顯得格外清脆。月亮升起來,他們走到睏乏,便點起火堆。壘石灶、收集引火的乾柴、煮水,每一件事都透著默契,卻不曾有誰先開口。 半寐半醒的時候又下起雨來。他打一個激靈,猛地起身,卻看見熄滅的火堆旁被人用焦灰寫下:“讓我們繼續迷路吧。我還想和他多待一會兒。或者讓我們再迷路一次、幾次,千萬次。” 他愣在那兒。傲慢又自卑的牧羊人從未在乎過羔羊的想法,自以為那是馴服。 他怎麼能把愛當作是馴服! 他衝入雨中尋找。 淋得濕透的兩個人在雨勢最盛的時刻相聚了。彷彿被這大雨衝昏了頭腦,他們手足無措,也不知該如何表達,乾脆就原始地狂奔著,呼喊著彼此的名字,直到筋疲力盡地去泥濘裡倒成一團。 原來你早就在這雨裡了,原來我也早就在這雨裡了!原來我們本不必躲藏的,只要淋濕就好了!只要沈浸,只要赤誠地愛就好了! 泥地裡留下了他們重新擁抱的痕跡:兩個看不清四肢的模糊人形。 他提議:“應該在這裡寫第九封信。” “寫什麼好呢?” “就寫:‘我們不要躲雨了’。” 此後的路上雨水更加豐沛,他們沒再躲雨過,新生的草木也肉眼可見地繁茂起來。路旁的梨樹上落下熟得過頭的果實,散髮著酒氣般的甜香。某個時刻,兩個人不約而同地停下,仰躺在一片青草地上。 “不走了吧?”戀人問。 “是的,不走了,就在這裡變老吧。” “那還寫信嗎?” “在死去之前——在彼此還能交談的所有時間裡,我們的話語就是信。也許有些時候說不出來什麼,也並不說話;那我們各自的存在、我們的家,還有這片草地,都是信。” “除了你我,還會有誰來讀嗎?” “會有的。只要他們也離開了銀色荒原。” |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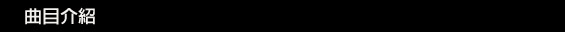
CD 1
| 曲序 | 曲名 | 演唱人 |
| 1 | 銀色荒原 | 裘德 |
| 2 | 火山灰 | 裘德 |
| 3 | 春天的臨終 | 裘德 |
| 4 | 飛鳥在風暴中 | 裘德 |
| 5 | 奇卡奇卡 | 裘德 |
| 6 | 變色龍 | 裘德, 吳青峰 |
| 7 | 沒有羊的牧羊人 | 裘德 |
| 8 | 請求迷失在七月森林 | 裘德, 孫盛希 |
| 9 | 我們不要躲雨了 | 裘德 |
| 10 | 尋找一片青草地 | 裘德 |